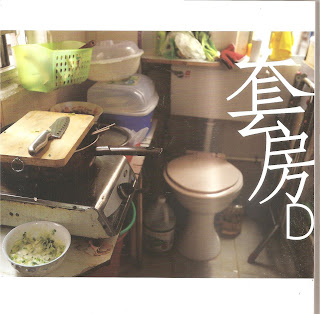小说家笔下的美国社会缩影
(南方都市报: 南方阅读 视野 2012-02-26)
摘要:打开乔纳森·弗兰岑(台译强纳森·法兰岑)这本厚厚的第四部小说《自由》(Freedom),令人悠然想起早已著作等身还曾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利普·罗斯,这里想说的是后者的成名作《美国三部曲》,以及罗斯在小说中重构近数十年间的美国知识分子家族史。
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打开乔纳森·弗兰岑(台译强纳森·法兰岑)这本厚厚的第四部小说《自由》(Freedom),令人悠然想起早已著作等身还曾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菲利普·罗斯,这里想说的是后者的成名作《美国三部曲》,以及罗斯在小说中重构近数十年间的美国知识分子家族史。因为题材吃力不讨好,而且有野心的小说家都偏好于文学新体裁的实验,目前创作这类社会传记体写实小说并跻身大作家之列的为数不多,弗兰岑继《纠正》后以《自由》这部小说,继续探索从性别观、婚姻和家庭生活,展现美国一代人的心智成长之路。
与菲利普·罗斯等大作家相比,也许弗兰岑的文学个性稍弱,但在贴近美国日常生活的描写上毫不逊色,以这本《自由》为例,它讲述一位美国女孩的成长历程,里面穿插了许多政治、运动及娱乐活动背景,亦充斥不少美国流行文化意涵,这些流行文化元素尽在充满幽默感的文字中表露无遗,菲利普·罗斯那不无挖苦的小说文字表达出沉重的语感,在这方面弗兰岑比这位文学前辈来得比较轻逸,但他的文学雄心同样不凡。在他的散文集《如何独处?》(How to be alone)里,读者不会忘记那篇曾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偶尔做做梦》(Perchance to Dream),他在文中指出布什政府反恐战争时期的媒体氛围带来美国文学的衰落,并提出小说家有义务以社会写实风格创作小说,而弗兰岑的小说如《纠正》和《自由》正是这位纽约客评论家的大胆尝试。
不管弗兰岑复兴社会写实小说的尝试与罗斯等作家有何分别,这部小说也像许多美国小说家的故事般,采取了一种“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框架,但它更多围绕在佩蒂和沃尔特·伯格兰夫妇及其子女在成长、家庭及与邻居关系上的微妙心理变化上,也触及美国家庭对于性宽容等问题的态度。书中女主角佩蒂自幼成长于小康家庭,父亲为律师,母亲参与政党,身为姐姐的她是篮球校队成员而习惯身体训练,而她曾在中学生举办的派对中被强暴,她与大学同学伊利莎有过暧昧的同窗之谊。如此的身心经历,冲击着这位在自由派中产家庭长大的女孩,变成后来的佩蒂·伯格兰,恰好其儿子乔伊天生反叛母亲的性格并亲近该位性开放的女邻居及其女儿,小说第一部分“好邻居”的“错误已经铸成(佩蒂自传)”一章便道出这对母子的纠纷原因,佩蒂因为儿子乔伊经常在一位打扮俗艳的邻居卡洛尔家中流连,当佩蒂全力照顾卡洛尔的女儿康妮时,卡洛尔却没理会她的女儿洁西卡,只顾与佩蒂的儿子亲昵,于是佩蒂气得发疯。
佩蒂虽生于自由开放的中产家庭,可是父母对这位长女的注意从来比不上对其他妹妹的呵护,在佩蒂童年时,他们讥笑她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在佩蒂参加派对被同学强暴后,作为律师的父亲仅与施暴者父亲谈过一通电话,然后向她覆述施暴者认为双方你情我愿下发生关系的辩解,对女儿坚持曾经反抗的话,冷冰冰地报以“胜诉机会不高”之类的专业辞令,仿佛那是他的顾客而不是女儿似的。如此冷淡的态度,加上自幼被认为愚蠢,在她身上发展出两个自相矛盾的自我,一面是谦逊,另一面是自私易怒。透过伊利莎介绍,她参与学生举办的摇滚派对,认识那为她所倾恋、却风流成性的独立摇滚乐手理查·卡兹,在派对中她遇见许多抽大麻的人,但也邂逅了理查的好友兼忠实粉丝沃尔特,当沃尔特告诉她伊利莎吸食海洛英致死的消息后,两人渐渐开始了恋情,两人在佩蒂毕业后不久结婚,这个故事其实对许多自大学相识直至成家立室的夫妻来说并不陌生,大部分夫妻都是一人忍受另一人,正如好好先生的沃尔特默默忍受喜怒无常的佩蒂。
当然,书中故事也是不少家庭悲剧的来源,例如女方在成长过程的内心郁结和男女双方认识的背景,都导致日后的家庭冲突。艺术天分平凡的佩蒂,在重视自由的中产家庭得不到宠爱,这形成她日后从心底排斥行为开放的邻居,也造就她对“家庭”这种传统价值的坚持:她那些自由派的妹妹们日后变成孤独生活、性格乖僻的艺术家,而她则为自己能成家立室而自豪;当然,被强暴的记忆也造成性压抑。其实,许多坚持家庭伦理的保守分子也曾在成长中试过许多挑战社会的大胆事情,但来自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挫折感,将他们的观念推向传统保守。
《自由》是一部典型的当代美国小说,从揭开第一页起,读者会得到“内容很政治”的印象,因为主角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莫不受学校甚至家庭环境所支配,而他们的成长岁月,亦往往充斥着来自家庭的自由开放观念和道律约束对一切“政治不正确”的个人爱憎进行压抑,书中角色的谈话或者关心的课题亦大多围绕在政治或社会议题上,即使涉及性也不是令人想入非非的描写,而是对他人的闲聊,或者青年交际的新鲜话题(例如在第二部“2004”的“女人世界”一章,乔伊进入大学时同学的性话题),或者充满政治意味的讨论,作者的幽默笔法也政治意涵,如乔伊原本爱上康妮,当他离乡入读大学后彼此不再见面,作者便说“目的是要发展出各自独立的自我,看看这两个独立的自我是否仍可以好好配对”。连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也有一个政治化的名字:“自由市场培养竞争”,而这一章的“竞争”其实是指家庭问题。
虽说坚守写实主义风格,但《自由》一书仍采取了独特的写法,小说各章从不同面向描述伯格兰家庭,不少篇章以对话为主,其中有关佩蒂的篇章显示她患上抑郁症,然而她用了第三人称,却仿佛抑郁症病人在心理医生要求下撰写自传,也许暗示这位成长于自由家庭的典型美国人已无法与读者交流,一如美国有太多没法与人交流的价值观。作者在“2004”第四章“六年”开始处作出交代了第三人称的意图,佩蒂在这一章最终决定与丈夫分开六年并与理查·卡兹同住。
究竟《自由》有没有实践作者在《偶尔做做梦》中提出的主张?弗兰岑在文章里批判了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等以边缘性质题材写作小说的习惯,而《自由》的主人公就代表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失乐园”经历。《自由》的故事背景也呼应着作者的生平,伯格兰一家的住址被设定在圣保罗镇,有论者认为,这个南方贫穷小镇的名称恰好呼应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费茨杰拉德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而弗兰岑自己也在圣路易市出生,而且与故事主角一样有瑞典人的姓氏。
小说最终或许引起读者的疑问:不管小说之目的在于奇异感或写实,最上佳的小说总能扣动读者的心弦,但在世界各地,这类以个别社会文化背景为题材的作品能够打动多少非美国读者的心?但那些对美国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他们会在《自由》的生活世界里找到一种真正属于美国文化的旨趣,这些细节建构出一个真实的当代美国。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